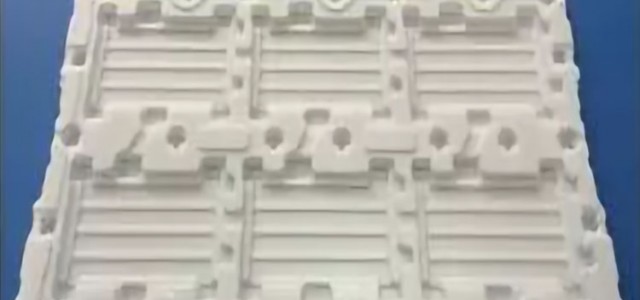那一年的冬天,我們正要從丹娜麗芙島搬家回到大迦納利島自己的房子里去。
一年的工作已經(jīng)結(jié)束,美麗無比的人造海灘引進了澄藍平靜的海水。
荷西與我坐在完工的堤邊,看也看不厭的面對著那份成績欣賞,景觀工程的快樂是不同凡響的。
我們自黃昏一直在海邊坐到子夜,正是除夕,一朵朵怒放的煙火,在漆黑的天空里如夢如幻地亮滅在我們仰著的臉上。
濱海大道上擠滿著快樂的人群。鐘敲十二響的時候,荷西將我抱在手臂里,說:“快許十二個愿望,心里重復著十二句同樣的話:“但愿人長久,但愿人長久,但愿人長久,但愿人長久——”
送走了去年,新的一年來了。
荷西由堤防上先跳了下地,伸手接過跳落在他手臂中的我。
我們十指交纏,面對面地凝望了一會兒,在煙火起落的五色光影下,微笑著說:“新年快樂!”然后輕輕一吻。我突然有些淚濕,賴在他的懷里不肯舉步。
新年總是使人惆悵,這一年又更是來得如真如幻。許了愿的下一句對夫妻來說并不太吉利,說完了才回過意來,竟是心慌。
“你許了什么愿。”我輕輕問他。
“不能說出來的,說了就不靈了。”
我勾住他的脖子不放手,荷西知我怕冷,將我卷進他的大夾克里去。我再看他,他的眸光炯炯如星,里面反映著我的臉。
“好啦!回去裝行李,明天清早回家去羅!”
他輕拍了我一下背,我失聲喊起來:“但愿永遠這樣下去,不要有明天了!”
“當然要永遠下去,可是我們得先回家,來,不要這個樣子。”
一路上走回租來的公寓去,我們的手緊緊交握著,好像要將彼此的生命握進永恒。
而我的心,卻是悲傷的,在一個新年剛剛來臨的第一個時辰里,因為幸福滿溢,我怕得悲傷。
不肯在租來的地方多留一分一秒,收拾了零雜東西,塞滿了一車子。清晨六時的碼頭上,一輛小白車在等渡輪。
新年沒有旅行的人,可是我們急著要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。
關了一年的家,野草齊膝,灰塵滿室,對著那片荒涼,竟是焦急心痛,顧不得新年不新年,兩人馬上動手清掃起來。
不過安靜了兩個多月的家居生活,那日上午在院中給花灑水,送電報的朋友在木柵門外喊著:“Echo,一封給荷西的電報呢!”
我匆匆跑過去,心里撲撲的亂跳起來,不要是馬德里的家人出了什么事吧!電報總使人心慌意亂。
“亂撕什么嘛!先給簽個字。”朋友在摩托車上說。我胡亂簽了個名,一面回身喊車房內(nèi)的荷西。
“你先不要怕嘛!給我看。”荷西一把搶了過去。
原來是新工作來了,要他火速去拉芭瑪島報到。只不過幾小時的光景,我從機場一個人回來,荷西走了。
離島不算遠,螺旋槳飛機過去也得四十五分鐘,那兒正在建新機場,新港口。只因沒有什么人去那最外的荒寂之島,大的渡輪也就不去那邊了。
雖然知道荷西能夠照顧自己的衣食起居,看他每一度提著小箱子離家,仍然使我不舍而辛酸。
家里失了荷西便失了生命,再好也是枉然。
過了一星期漫長的等待,那邊電報來了。
“租不到房子,你先來,我們住旅館。”
剛剛整理的家又給鎖了起來,鄰居們一再的對我建議:“你住家里,荷西周末回來一天半,他那邊住單身宿舍,不是經(jīng)濟些嘛!”
我怎么能同意。匆忙去打聽貨船的航道,將雜物、一籠金絲雀和汽車托運過去,自己推著一只衣箱上機走了。
當飛機著陸在靜靜小小的荒涼機場時,又看見了重沉沉的大火山,那兩座黑里帶火藍的大山。
我的喉嚨突然卡住了,心里一陣郁悶,說不出的悶,壓倒了重聚的歡樂和期待。
荷西一只手提著箱子,另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向機場外面走去。
“這個島不對勁!”我悶悶地說。
“上次我們來玩的時候你不是很喜歡的嗎。”
“不曉得,心里怪怪的,看見它,一陣想哭似的感覺。”我的手拉住他皮帶上的絆扣不放。
“不要亂想,風景好的地方太多了,剛剛趕上看杏花呢!”
他輕輕摸了一下我的頭發(fā)又安慰似的親了我一下。
只有兩萬人居住的小城里租不到房子。我們搬進了一房一廳連一小廚房的公寓旅館。收入的一大半付給了這份固執(zhí)相守。
安置好新家的第三日,家中已經(jīng)開始請客了,婚后幾年來,荷西第一回做了小組長,另外四個同事沒有帶家眷,有兩個還依然單身。我們的家,伙食總比外邊的好些,為著荷西愛朋友的真心,為著他熱切期望將他溫馨的家讓朋友分享,我曉得,在他內(nèi)心深處,亦是因為有了我而驕傲,這份感激當然是全心全意的在家事上回報了他。
島上的日子歲月悠長,我們看不到外地的報紙,本島的那份又編得有若鄉(xiāng)情。久而久之,世外的消息對我們已不很重要,只是守著海,守著家,守著彼此。每聽見荷西下工回來時那急促的腳步聲上樓,我的心便是歡喜。
六年了,回家時的他,怎么仍是一樣跑著來的,不能慢慢的走嗎?六年一瞬,結(jié)婚好似是昨天的事情,而兩人已共過了多少悲歡歲月。
小地方人情溫暖,住上不久,便是深山里農(nóng)家討杯水喝,拿出來的必是自釀的葡萄酒,再送一滿懷的鮮花。我們也是記恩的人,馬鈴薯成熟的季節(jié),星期天的田里,總有兩人的身影彎腰幫忙收獲。做熱了,跳進蓄水池里游個泳,趴在荷西的肩上浮沉,大喊大叫,便是不肯松手。
過去的日子,在別的島上,我們有時發(fā)了神經(jīng)病,也是爭吵的。
有一回,兩人講好了靜心念英文,夜間電視也約好不許開,對著一盞孤燈就在飯桌前釘住了。
講好只念一小時,念了二十分鐘,被教的人偷看了一下手表,再念了十分鐘,一個音節(jié)發(fā)了二十次還是不正確,荷西又偷看了一下手腕。知道自己人是不能教自己人的,看見他的動作,手中的原子筆啪一下丟了過去,他那邊的拍紙簿嘩一下摔了過來,還怒喊了一聲:“你這傻瓜女人!”
第一次被荷西罵重話,我呆了幾分鐘,也不知回罵,沖進浴室拿了剪刀便絞頭發(fā),邊剪邊哭,長發(fā)亂七八糟的掉了一地。
荷西追進來,看見我發(fā)瘋,竟也不上來搶,只是倚門冷笑:“你也不必這種樣子,我走好了。”
說完車鑰匙一拿,門砰一下關上離家出走去了。
我沖到陽臺上去看,凄厲的叫了一聲他的名字,他哪里肯停下來,車子唰一下就不見了。
那一個長夜,是怎么熬下來的,自己都迷糊了。只念著離家的人身上沒有錢,那么狂怒而去,又出不出車禍。
清晨五點多他輕輕地回來了,我趴在床上不說話,臉也哭腫了。離開父母家那么多年了,誰的委屈也能受下,只有荷西,他不能對我兇一句,在他面前,我是不設防的啊!
荷西用冰給我冰臉,又拉著我去看鏡子,拿起剪刀來替我補救剪得狗啃似的短發(fā)。一刀一刀細心的給我勉強修修整齊,口中嘆著:“只不過氣頭上罵了你一句,居然絞頭發(fā),要是一日我死了呢——”
他說出這樣的話來令我大慟,反身抱住他大哭起來,兩人纏了一身的碎發(fā),就是不肯放手。
到了新的離島上,我的頭發(fā)才長到齊肩,不能梳長辮子,兩人卻是再也不吵了。
依山背海而筑的小城是那么的安詳,只兩條街的市集便是一切了。
我們從不刻意結(jié)交朋友,幾個月住下來,朋友雪球似的越滾越大,他們對我們真摯友愛,三教九流,全是真心。周末必然是被朋友們占了,爬山,下海,田里幫忙,林中采野果,不然找個老學校,深夜睡袋里半縮著講巫術和鬼故事,一群島上的瘋子,在這世外桃源的天涯地角躲著做神仙。有時候,我快樂得總以為是與荷西一同死了,掉到這個沒有時空的地方來。
那時候,我的心臟又不好了,累多了胸口的壓迫來,絞痛也來。小小一袋菜場買回來的用品,竟然不能一口氣提上四樓。
不敢跟荷西講,悄悄的跑去看醫(yī)生,每看回來總是正常又正常。
荷西下班是下午四點,以后全是我們的時間,那一陣不出去瘋玩了。黃昏的陽臺上,對著大海,半杯紅酒,幾碟小菜,再加一盤象棋,靜靜的對弈到天上的星星由海中升起。
有一晚我們走路去看恐怖片,老舊的戲院里樓上樓下數(shù)來數(shù)去只有五個人,鐵椅子漆成鋁灰色,冰冷冷的,然后迷霧凄凄的山城里一群群鬼飄了出來捉過路的人。
深夜散場時海潮正漲,浪花拍打到街道上來。我們被電影和影院嚇得徹骨,兩人牽了手在一片水霧中穿著飛奔回家,跑著跑著我格格的笑了,掙開了荷西,獨自一人拚命的快跑,他鬼也似的在后面又喊又追。
還沒到家,心絞痛突然發(fā)了,沖了幾步,抱住電線桿不敢動。
荷西驚問我怎么了,我指指左邊的胸口不能回答。那一回,是他背我上四樓的。背了回去,心不再痛了,兩人握著手靜靜醒到天明。
然后,纏著我已經(jīng)幾年的噩夢又緊密的回來了,夢里總是在上車,上車要去什么令我害怕的地方,夢里是一個人,沒有荷西。
多少個夜晚,冷汗透濕的從夢魅里逃出來,發(fā)覺手被荷西握著,他在身畔沉睡,我的淚便是滿頰。我知道了,大概知道了那個生死的預告。
以為先走的會是我,悄悄地去公證人處寫下了遺囑。時間不多了,雖然白日里仍是一樣笑嘻嘻的洗他的衣服,這份預感是不是也傳染了荷西。
即使是岸上的機器壞了一個螺絲釘,只修兩小時,荷西也不肯在工地等,不怕麻煩的脫掉潛水衣就往家里跑,家里的妻子不在,他便大街小巷的去找,一家一家店鋪問過去:“看見Echo沒有?看見Echo沒有?”
找到了什么地方的我,雙手環(huán)上來,也不避人的微笑癡看著妻子,然后兩人一路拉著手,提著菜籃往工地走去,走到已是又要下水的時候了。
總覺相聚的因緣不長了,尤其是我,朋友們來的周末的活動,總拿身體不好擋了回去。
周五帳篷和睡袋悄悄裝上車,海邊無人的地方搭著臨時的家,摸著黑去捉螃蟹,礁石的夾縫里兩盞鎊鎊的黃燈扣在頭上,浪潮聲里只聽見兩人一聲聲狂喊來去的只是彼此的名字。那種喊法,天地也給動搖了,我們尚是不知不覺。
每天早晨,買了菜蔬水果鮮花,總也舍不得回家,鄰居的腳踏車是讓我騎的,網(wǎng)籃里放著水彩似的一片顏色便往碼頭跑。騎進碼頭,第一個看見我的岸上工人總會笑著指方向:“今天在那邊,再往下騎——”
車子還沒騎完偌大的工地,那邊岸上助手就拉信號,等我車一停,水里的人浮了起來,我跪在堤防邊向他伸手,荷西早已跳了上來。
大西洋的晴空下,就算分食一袋櫻桃也是好的,靠著荷西,左邊的衣袖總是濕的。
不過幾分鐘吧,荷西的手指輕輕按一下我的嘴唇,笑一笑,又沉回海中去了。
每見他下沉,我總是望得癡了過去。
岸上的助手有一次問我:“你們結(jié)婚幾年了?”“再一個月就六年了。”我仍是在水中張望那個已經(jīng)看不見了的人,心里慌慌的。
“好得這個樣子,誰看了你們也是不懂!”
我聽了笑笑便上車了,眼睛越騎越濕,明明上一秒還在一起的,明明好好的做著夫妻,怎么一分手竟是魂牽夢縈起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