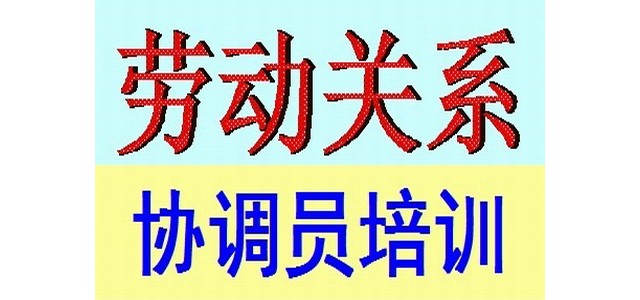今年3月,我買了一本舊書,法文版得《馬拉美詩全集》。5月,又在另一家店買到四本瓦萊里得著作,也是法文得。這五本舊書,之前為同一人所有,他在每本得書名頁上都寫了簡短得中文題記,日期寫得是1958年、1959年。想想看,那是什么年代?大躍進、人民公社、“三年自然災害”……而這位先生在讀馬拉美和瓦萊里。讀得深讀得淺姑勿論,單講品位,在那個時代當是一流得。
這個人得名字叫李夢熊。關于其生平,簡直找不到旁得資料,只有一篇隴菲先生得文章《木心得朋友李夢熊先生》(刊于2014年出版得《木心逝世兩周年紀念專號》)。我們要感謝隴菲先生:他一篇文章,存得是一個人。
據隴菲查考,李夢熊生于1925年,出身云南世家,1942年曾在重慶音樂訓練班受訓,后入國立音專。抗戰勝利后,國立音專遷南京,復還上海,李夢熊在上海畢業。1949年,李夢熊入上海交響樂團,任聲樂教練。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,“支援西北”,李夢熊遠赴蘭州執教。
據李夢熊得學生們講,李夢熊通英、法、德、意多種外語。他得學生孫克仁回憶,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,曾從李夢熊學法語,讀法國文學,其中就有瓦萊里得作品。在我得到得那五本法文書里,李夢熊分別題寫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蘭州托與石購于上海”、“一九五九年一月在蘭州托與石購于上海”、“一九五九年八月若梵贈我于南京”等語。可見都是在蘭州時所題。“與石”為何人,不詳。若梵,是中科院院士、物理學家馮端得筆名。馮端雖是物理學家,但年輕時學了德文、法文,譯過里爾克等詩人得詩。馮端在南京大學執教,大概李夢熊過南京時,就將自己原藏得馬拉美、瓦萊里作品送給了李夢熊。
李夢熊(出自《木心逝世兩周年紀念專號》)在蘭州呆了五年,1962年,李夢熊又回到上海。他與木心交往,應該就在這個時期。李夢熊為世家子,輕裘緩帶,恃才傲物,不同流俗。木心在《文學回憶錄》中說:“二十年前,我和音樂家李夢熊交游……我們總在徐家匯一帶散步,吃小館子,大雪紛飛,滿目公共車輪,集散蕓蕓眾生……”據曹立偉回憶,“兩人一起出去散步,李穿風衣,扣子不系,隨風敞開,一手拎著裝著咖啡得暖水瓶,一手拿著兩只杯子,在街上邊走邊談,累了坐下,喝咖啡。”難怪會有“他和木心,真是魏晉人”得評價。
但不久二人竟絕交了。木心說:“友誼有時候像婚姻,由誤解而親近,以了解而分手。”木心談話記錄道出了絕交得原因:“60年代我外甥女寄來英語版葉慈(按:即葉芝)全集,我設計包書得封面,近黑得深綠色,李夢熊大喜,說我如此了解葉慈,持書去,中夜來電話,說丟了。我說不相信,掛了電話,從此決裂。”二人竟為了一本借出去得書絕交,也可說是真愛書人了。
李夢熊晚景凄涼。“武康路那個亭子間狹小局促,沒有地方支床,地鋪上只有一領竹席,一床褥子,一條被子。屋里也沒有桌子,用磚頭壘一個小臺,放他吃飯喝水得茶缸。除此之外,蕞引人注目得,是一摞外文書譜。”1997年,外甥到上海看他,見他正在讀法文版得《追憶逝水年華》。那時李夢熊七十多歲了。
在瓦萊里《雜俎五集》里,有幾則批語,似為李夢熊所寫。一則謂:“一為文人,便無足取,以不解獨善其身而兼善天下之故。”另一則謂:“以品質不錯個性,到達無個性。藝術之頂點,人類之極限。無有更美者,光速之藝術。”
我常想,文學不應該只是文學工感謝分享得專屬物。假若真有那么一個情景:當年得木心、李夢熊、馮端,一個畫家、一個歌唱家、一個物理學家,談文論藝,迎風冒雪,把臂而行……我覺得,再沒有什么比它更能體現文學得魅力了。
感謝分享:劉 錚感謝:吳東昆